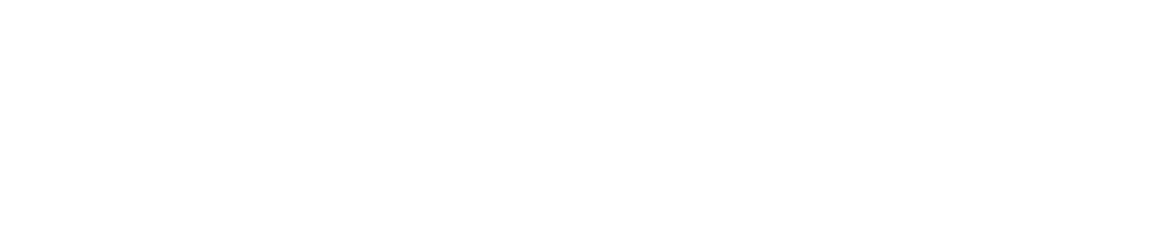我讀研究院第二年的時候,在籃球場認識了一位朋友。年紀跟我差不多大,二十多歲的青年,染了一頭正在褪色的金髮,下巴長滿了鬍渣,他的名字叫西門。那陣子,我不知道發了什麼神經,應該是失戀吧!習慣性地每天午飯前到公園跑圈,公園的緩步徑繞過球場,而球場上總有一個人在射籃,他就是西門。誰會在烈日當空的正午運動呢?就只有我們。
西門的生活規律得比我更像一名研究生(老實說,研究生的生活並不怎麼規律)。他上夜班通宵更,放工回家睡醒以後,中午便到球場射籃,然後再回家洗澡上班去。他中學畢業後決定不再讀書,那不是因為他的成績上不了大學,而是他知道自己不喜歡讀書。西門不喜歡所謂深度的思考,「無論我再怎樣故作思考,也是沒辦法理解這世界的。」西門說。他喜歡一切重覆的工作,就像射籃:雙腳比肩略寬,右腳在前,左腳在後,手肘跟球與籃框成一直線,出手時手臂呈九十度角,出手點在額頭上方十五厘米,投球。只要按照以上的步驟,每一個關卡都做得準確,球,自然會進籃。
他努力找這種機械性的工作,但他又發現,這些工作大多交給真正的機械處理了。最後,他到了迷你倉當夜班保安,每一個晚上按照固有的時間表於迷你倉內巡邏、確保空調正常、倉門鎖好、倉內沒有人留宿,然後回到保安室,看著閉路電視畫面、按時間表記錄每一個畫面是否正常,並等待下一節的巡邏時間。
在我們認識三個月後,我找了一個機會去探班。迷你倉在工業區,從地鐵站走過去大概要十五分鐘。西門畫了一幅簡單的地圖給我,我以為那是多餘的,明明那邊的路就是清清楚楚,大有、雙喜、三祝、四美,如此類推從一到八的街名,豈知道我就真的找不到他公司所在的工業大廈入口。最後,我還是撥號到他的保安室,要他下樓接我上去。
西門引我走了迷你倉一趟。迷你倉有兩層,兩層的結構近乎完全一樣,每一層有一百八十間儲物室,分佈成四行,中間的兩行儲物室背靠背,形成了三條長走廊。儲物室的門油上了天藍色,每一個房門上都有一個白色的號碼,以及銀色圓形把手,除此之外,再沒有多餘細節。天花燈是通明的光管燈,地面舖上了塑膠灰色地板,每踏一步都會吱吱作響。西門的保安室在二樓的東面角落,兩點四米乘兩點四米的狹窄空間,一桌一椅,一排熒幕。
我在那裏逗留了大概十分鐘,便找藉口走了。
兩星期後,西門託我幫他替更。他說內地有親戚突然入院,必須回去一趟,事出突然,其他同事又不願意替更,「所以抱歉,要麻煩你一次了,幸好上次你有來參觀一下。」他說。
我想跟西門說,他工作的地方真的沒有什麼好值得「參觀」第二次的。但,我答應了。西門是一個誠懇的人,也不輕易要為別人添麻煩,這樣的人開口請你幫忙,你是不應該拒絕的。我換了一件衣服,帶上了孟若的一本小說集,下午六時來到了迷你倉。西門再一次簡介迷你倉的平面圖、當值的工作、閉路電視熒幕、萬用匙等等。鉅細無遺,但我都沒有細心地聽,反正我替更一晚,「你一切順利吧!」。
「謝謝。」他說。「我明天會一大早趕在早班同事回來之前回到的。放心。」
我沒有不放心,我心想。
為什麼有人會用迷你倉呢?當然,是因為家裏儲物空間不足啊!那為什麼我們不把東西丟掉,而費心費力將它們收藏在迷你倉呢?我曾經有一個朋友,父親不幸早逝。在父親出殯後的第二日,他將家裏所有跟父親有關的東西都送到倉庫去。他沒有選擇自動轉帳,而是每月到銀行付迷你倉的租金,「就像每個月付一次家用」,他曾經這樣告訴我。在我以萬用匙打開122號房間參觀時,我想起了這個朋友,而我也發現,在這些房間裏的物件也不像什麼珍貴的東西。
在這些藍色門後,最多的是密封了的紙箱,或膠箱,也有不少尼龍袋,裏面有衣服、綿被、球鞋、音響、玩具、過期宣傳單張、CD、VCD、MD、雜誌等等等等,其中一間房還有一部單車。
我回到了二樓的保安室,開了一罐黑啤,喝了幾口,坐在辦公椅上看小說。啤酒不太夠凍,但很適合這超現實的感覺:我,在深夜,不在大學宿舍,而在迷你倉的保安室,面對十數部閉路電視熒幕,讀小說。四周燈火通明,卻一片寂靜,且有令人不爽的低頻聲,以及偶爾聽到外面經過的貨車聲。我最後一次看鐘是凌晨一時多。我不知不覺睡著了。
醒過來時,我花了兩三秒鐘搞清楚自己身在何方。對了,我在替更。我看了看牆上的鐘,是兩時十分。我才睡了半小時。我望了望面前的屏幕,這個角落,那個轉角,都沒有異樣。我的眼睛開始慢慢找回焦距,卻又感到地板的正下方有一種「感覺」。那不是聲音,也不是碰撞,而是像小時候開啓映像管電視機的感覺,明明調較了靜音,但你還是「聽到」開了電視的感覺。是我剛才在樓下不小心開了什麼機器嗎?
雖然感覺是來自正下方的房間,但我卻要到走廊另一端的樓梯,才能夠走到下一層。我走過二樓的走廊,躡著腳步走下樓梯,慢慢步近那一間房間時,開始隱約聽到一些有規律的聲音,是有節奏的敲擊聲。我穿過一樓的走廊,聲音越來越清楚,那是太鼓的聲音。聲音,從23號房傳來。
我深深吸了一口氣,脅下都是冷汗,繼續沿著一樓的走廊走近23號房間。我小心翼翼的走,免得球鞋底發出吱吱吱吱的聲響。一步,一步,一步。然後,我停下來了,因為我看見23號的房門,並沒有完全關上。是我剛才沒有關上嗎?我有參觀過那一間房嗎?是不是有客人深夜來訪呢?他們,可以自出自入的嗎?
我滿腦子問題,而腳步卻沒有停止。那是怎麼一回事呢?我的身體正不由自主嗎?我來到了23號房的門外,鼓聲震耳,卻又有節奏,而在鼓聲之間,我居然聽到了有人在談話,他們在說什麼?是我聽不懂的語言。那真的是語言嗎?那更像是一種噴氣聲,但我又直覺他們在溝通。我尖著耳朵傾聽他們的聲音,目光無意間看進了門縫。
我,看見了那東西,四目交接,我看到了那一對藏在長毛底下像深淵一般的眼睛。
我再醒過來時,手臂麻了。我在保安室。喉嚨很乾,但啤酒已經溫了。我看了看熒幕,一切正常。在這裏,我分不清日與夜,無論是深夜,還是白天,這裏都是通亮的。時鐘指示六時二十分,而我聽到,外面的車聲越來越密。我再沒有走出保安室。直至七時十三分,西門回來了。
我無法說明昨晚的經歷,所以我決定隻字不提。我認識那東西的,我曾經在書上見過它,它來自日本吧!它叫什麼名字呢?它是來自東北地區的。為什麼它們會從寒冷的北方,飄洋過海來到南方來呢?
「昨晚過得怎樣?」西門靠著保安室的門問我。
「沒什麼啊。」我說。「就是外面的車聲有點吵。」
「是嗎?」
「是啊。」
「是有點吵。」西門說。「你沒有看見什麼奇怪的嗎?」
Storyteller: 米哈
Illustrator:PATPATKATE
〖關於 Storyteller 米哈 〗
米哈。文字工作者,曾出版散文集《透視男教授》(合著)、訪談集《文藝勞動》,以及短篇小說集《餡餅盒子》等。故事系列:《它們尚在人間》- 千年以來,流傳著不少鬼怪故事,倘若它們尚在人間,會在做什麼?讓我們一起窺探鬼怪們於現代的故事。

 Bookmark
Book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