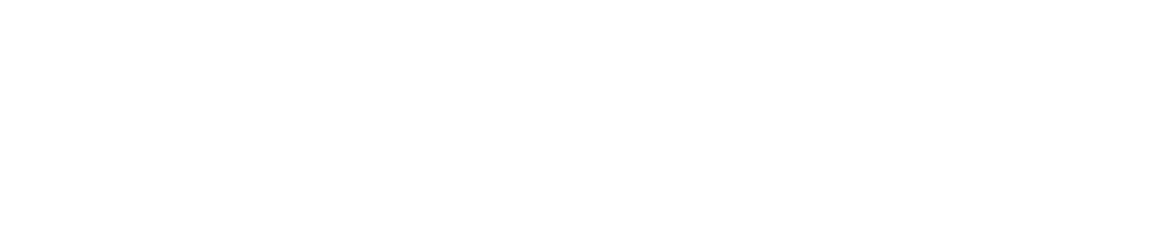那年中三。課室壁報張貼的全班合照,班主任的臉上多了一道原子筆痕。
那道疤痕,很深。
班主任用了整整一堂的班主任課,痛斥班內那個行兇學生是殘酷而冷血的,這次是劃花照片,下次就是用刀劃花她的臉。「這是非常嚴重的罪行,如果你還有良心,現在就站起來,當著全班面前自首吧!」
沒有人站起來。
班主任滿臉通紅的,眼睛睜得很大。
班主任教中文。每一天都有中文課,她就每一天都講,中文教的是品德,一個人的中文成績再好,寫文寫得再有感情,有甚麼用?「你的心是冷血的。」
他的中文成績最好。他很喜歡寫文章。他沉默,不社交。班主任說,誰是兇手,她心裡有數。她認定了他是兇手。他竟然厚臉皮得──她已經天天都在狠狠罵他了,他仍舊一臉安然,如常生活。
「自首吧!我叫你自首啊同學!」她生氣得向著麥克風大喊。
這樣不行。她惟有在每天放學後,相約班上不同的小圈子,哭訴自己終日擔驚受怕。「你們一定要保護老師,一起排斥他。」
你知道是他做,為何不直接罰他?「我要給他機會認錯。」
同學點點頭。她從來是校內最受歡迎老師之一,不無原因。
放學後,與小圈子訴苦前,還要約他到教員室門口,一個最大風的位置。「你在這裡站一會,我回來前,不能走開半步。」那是二月,天寒。他從四時站到七時,看著學校的燈一盞盞熄滅。天全黑,學校全黑。她挽著手袋,施施然從教員室走出來。
「很冷嗎?你的心更冷。」
「你有話跟我說嗎?」
「你聰明!你就一直沉默!」
她離開。換訓導主任出來。
「她告訴我了。你簽紙認罪,記一個大過。你不認罪,可能會踢出校?」
班主任約見班上每個同學,要他們選擇,幫她或幫他。
他每天回學校,回課室,都見同學議論紛紛。他很不安,如常孤獨。他不知道發生甚麼事──猜到與自己有關,但不敢問,也不敢偷聽。
「太小題大造吧?」
「我跟他無交情,但也無仇啊。」
班主任再三強調,學校是教人明辨是非的地方,同學一定要站在善的一方,懲罰惡人。
如常,中文堂,班主任一入課室,就叫他罰站。他站起,幾個同學也立即站起來,怒目著她。她一怯,叫他們全部坐下。如常,她叫他放學後到教員室門外罰站,幾個同學也跟來了,不斷叫她出來,她沒有出來。同學叫他走,「我們在這裡等她。」
以後,她沒再罰他,沒再提起兇手與自首,壁報版上的合照也消失了。
彷彿,一切不曾發生。
一天放學,他在校門外暈倒,第一個經過他的,是班主任。幾個同學截停了她,「幫幫他啊!」「我趕著吃飯,飯後回校開會,我時間很寶貴。」說罷,她挽著好姊妹老師的手,有說有笑地走了。
同學召救護車,送他到醫院。他的母親來了,同學求他母親向學校投訴。
「你們心胸可否寬一點?我一來,他一醒,你們就要投訴老師!」
他病好,升高中,畢業了,因公開試成績最好,便要回到中學頒獎台上,向著全校師生,感謝學校栽培。
他出來工作很久了。她一直在學校任教。
彷彿,一切不曾發生。
Storyteller:趙曉彤
Illustrator:Jennie Yu

 Bookmark
Book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