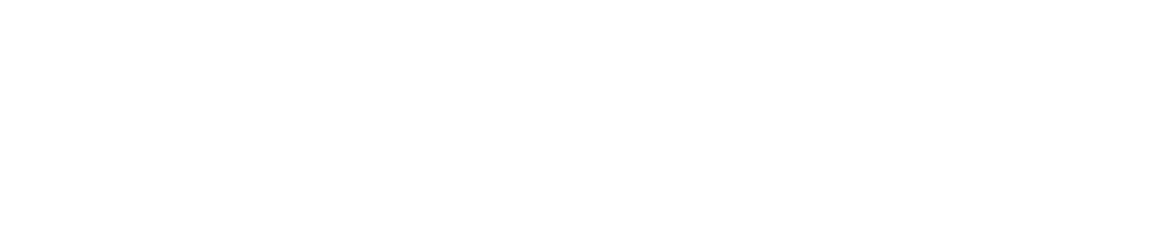白只記不起那晚後來的事情,甚至懷疑這就是所謂的創傷後遺症。十七歲那年,他考進了演藝的戲劇學院,自問對演戲不怎樣有熱情,亦不熱衷舞台,只是神差鬼使地踏進了校門。
學校規矩:一年級生不能踏台板,只能當後台人員,認識劇場運作。實際上,他的工作就是「呆等」。他會跟同學到咖啡店,攪拌啞黃的咖啡,看着裝酷的咖啡師,想像他是個怎樣的人,也想像自己會變成怎樣的人,打發下課後的時間,等待學校綵排結束。那時的他不在意咖啡有多甘醇可口,純粹為了提神,好熬到凌晨一點,回學校取修改好的劇本去影印。
那晚,他回到學校,接過綵排後被修改過的新劇本,匆匆拿去影印。他整個人迷糊昏沉,只想着要快點離開。幸好影印不是難事,把劇本一把塞進影印機,繼續跟旁邊的同學打鬧嬉罵,支撐疲憊的雙眼。
在快印好四十份劇本之際,同學拍拍他的肩,問他到底在印什麼。他走近影印機,看見一張又一張嗖嗖而出的白紙,當下意識到自己做了蠢事,一片空白。
腦海飛快閃過幻燈片,預告接下來要做的工作:到辦公室解釋怎樣印錯了劇本,拜託職員把影印卡重新增值⋯⋯但辦公室關門了,要待到明早開門⋯⋯但劇本又要趕在中午綵排前派送到所有人手上,所有人都在等待這劇本⋯⋯
他捧着那三千多張白紙,輕敲主管的房門,說:「印好了。但我全印了白紙。」聲音帶顫抖,不能似《踏血尋梅》丁子聰自首時般冷靜。至於之後的事態發展,他已經全然忘了。
這事沒使他悟出什麼大道理,繼續蹺課、熬夜、喝咖啡,在渾噩中度日,練習如何連吃兩個碟頭飯而面不改容。然後畢業,組了樂隊,當上演員。「白只影白紙」成了他與同學「話當年」時定會提到的一件蠢事。這事就似人生中一塊可有可無的骨牌,即使拿掉了,其他的骨牌也不會順勢倒下。
但正是一件件無聊又沒意義的蠢事,點滴累積成他的人生,他才憶起學校時光沒有白過,他曾是如何的快樂。
Storyteller:白只
Text:Storyteller
Illustrator:CY Lai

 Bookmark
Book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