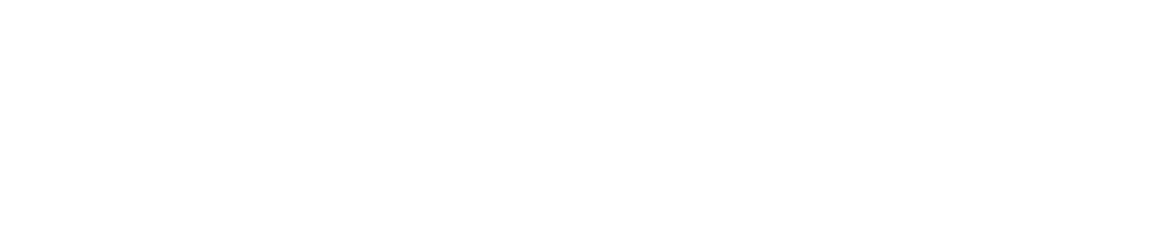白色窗紗翩起,風鈴的鐵片清脆地相互碰擊,風要來了。
這是樹海深處的一間小屋,是陽每年暑假都來避暑的地方。不過,與其說避暑,不如說是避世。今年,他厭倦了庸碌的城市生活,於是狠下心腸辭掉自然科學教師的工作,決定在樹海裏住上好一段時間,完成藏在肚子裏,計劃已久的小說。
每逢颱風季節,風雨欲來之時,即使是樹海中央,溫度也可以高達三十度。儘管說來避暑,但陽也享受這樣炎熱的樹海。他喜歡站在高聳的樹叢之間往上看,看陽光透過葉隙照出悄悄在蒸騰的水氣,聽蟬鳴從四面八方聲嘶力竭地襲來,嗅泥土、植物、水點與太陽密鑼緊鼓的降雨計劃。預測每天的降雨機率與時間,是他感受大自然的方法。
樹海裏懂氣象的不止他一個,還有老是跑到陽屋頂來的山貓。不過,牠腳步很輕,即使走過那些竹瓦片搭成的屋頂也不會作聲。幾次大雨過後,陽一次外出回來,發現濕漉漉的牠躲在屋後簷蓬的一角,他才知道山貓的存在。這樣幾次後,每逢風雨將至,陽都故意打開氣窗,好讓山貓能竄進來避雨。
這次陽回到小屋數天,天盡是放晴,一直未見山貓。聽到風鈴鐵片碰撞的聲音漸趨頻密,他簡直樂透了。陽及早準備了好幾個山貓喜歡的沙甸魚罐頭,喇叭奏起輕爵士,還有預備多一把風扇,因為愛避暑的,不只他一個。
白色窗紗翩起,風鈴的鐵片拼命相互碰擊,雨終來了。
陽把屋的氣窗都打開,如常寫着小說。雨滴答滴答打着屋頂,風很大,他突然想到他不在的時候,山貓一直獨個兒面對這樣的天氣,他感到內疚。但又想到這本是這野貓習慣的生活,自己的來臨與這屋子的存在,於貓而言本來無關重要,甚至是對牠家的一種強行侵佔。他期待着山貓的到來,但同時又想到自己,也正是因為討厭被與己無關的人事介入而選擇走到這樣偏遠的地方生活的。
因此陽沒有再想着山貓,但雷聲與閃電交加使他煩燥,他泡了壺花茶喝着喝着就睡了。
貓果然沒有來,陽翌日清晨像第一次遇見貓時那樣走到屋後找牠,但那只有一堆尚未開花的鼠尾草。他想山貓應該已經忘記他了,況且,貓沒有責任在陽回來時乖乖回來,儘管非常失望,但陽知道自己要給予貓自由選擇的時間。於是隨後每天,他都掛起雨天娃娃,希望雷雨每天都來,貓才有機會來找他。
沙甸魚罐頭,開了又蓋上,幸好是罐頭,不容易變壞。陽想起去年夏天,離開時,他把所有剩下的罐頭打開,全部送給山貓,待牠肚餓時自己吃,但山貓彷彿能意會到甚麼般,一個也沒有吃,只竄到屋子的一角板着臉蜷縮着。收拾行李後,他知道不可能把山貓待在家裏,於是花了很大力氣才把牠拖出房子,還被牠抓傷了手腳。山貓的嘶吼聲淒厲,但陽很生氣,一直指罵牠不要跟來,還用樹枝把牠打傷,山貓才站着不再追隨陽離去的背影。事後陽心感愧疚,但他認為自己是不可能把山貓帶回城市的,那貓本來屬於樹海,若他這樣做,他更加不能原諒自己。
此刻陽有點忐忑不安,他在想當時山貓會否失血過多或者細菌感染而死?他後悔那刻沒有為山貓包紥好傷口才離去。想到這裏,他不渴求山貓回來,只希望牠沒有因為自己而死去,但他知道是生是死,除非看到山貓的屍體,否則他也不可能知道的。
這樣好幾晚陽也夢到山貓,但都是重覆的惡夢。夢開始時,他重遇長大後的山貓,貓原諒了他,一下子跳到他的懷抱裏,然後是陽餵飼山貓的融洽畫面。這樣的日子維持了好一段時間,直至有天陽接到城市來的一個長途電話,他再次執拾行李,山貓於是在屋子裏四處抓刮,推倒屋子的許多東西。那是陽漸行漸遠的女友的來電,陽嘗試向貓解釋自己必須回到城市的需要,但貓沒有理會,如常跳這跳那地向陽表達着不滿。陽一怒之下拿起山貓,從高處擲向牆,貓的頭無情地淌血,四腳朝天,就那樣死了。
如是者陽好幾晚也沒睡好。這樣連續下了一星期的雨,貓也沒有回來。山貓就那樣消失了,他在想,或許貓本來從來也沒出現過。他知道山貓是不會再回來了,而且他害怕,如果貓回來,他會再一次那樣傷害牠。於是他決定放棄對貓的思念,把全部沙甸魚罐頭煮掉,專心寫作,把這頭山貓寫進自己的小說裏,以另類方式紀念牠。
不再回來的貓,失去聯絡,簡直像死掉了的人,所以自己更應該接受現實,他想。這樣獨居生活的自己,不與人聯絡,在許多人心中,也許也像個死人吧。沒有向人宣告死亡的喪禮,等於沒有跟人說「我要死了」的權利,這樣的離逝比正式的死亡更要可憐。不過陽意會到反正生和死彷彿都一樣,陽不介意這樣的生活了,因為這樣的「死亡」他活得更自在。
一週的大雨過後,天又重新放晴,氣溫回到廿一、二度的水平,蟬和鳥又悠哉地叫了起來。微涼的風默默吹來,風鈴愜意地偶爾碰撞,發出零丁幾下「叮叮噹噹」的聲音。陽往樹海裏看,他彷彿看見了那頭,嘴銜着魚的山貓站着,帶距離地看着他。
就讓牠去吧,他想。
Storyteller:野客
Illustratior:KungJengHang 龔正荇

 Bookmark
Book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