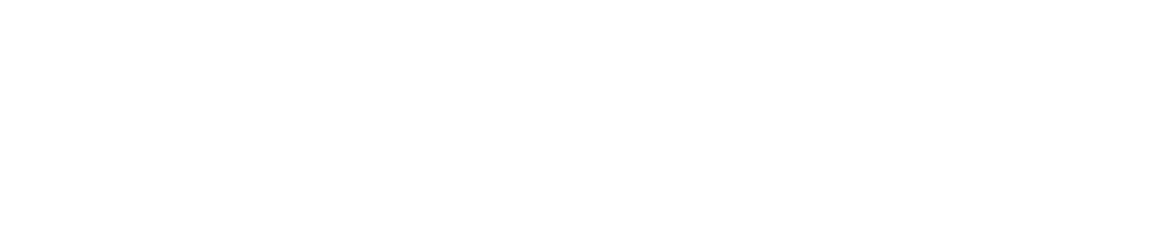雨嘩啦嘩啦地下,暴風吹得舖頭的玻璃櫥窗咚咚作響,我趕緊拉下鐵閘。天,水湧進來了,這是對我們五年沒擦地板的大懲罰嗎?我用毛巾和大力膠布封好門縫滲水的位置,嗚……後巷的積水幾乎浸到膝蓋以上了,那些在溝渠裏的老鼠蟑螂屍體都漂出來了,真是壯觀……
所有置在地上的「貨品」都浸濕了,我們忙着將不能浸水的盡量「拯救」。阿修累極抹一把汗,倚着放在舖頭中央的安全島,笑着用手語比着:「我們舖裏的無聊東西還真多啊─」這小子不會不記得,這個無聊又礙事的大玩具,是他哭得「涕淚橫飛」說要拾回來的吧?
「到底這次會不會掛八號以上的風球呢?」 阿修靈巧地跳坐在安全島上。
我印象中所有厲害的颱風通常都直接跳掛十號風球的,但就是有那麼一個叫杜鵑的九號颱風,我忘了是那個年份了。當時阿修只有五歲,咽喉裏的繭還沒有長成,還是個會哇哇大叫,放聲哭鬧的小鬼……
「杜鵑」來的時候,店裏的情況和現在幾乎一模一樣,當我在舖裏忙得要命和積水搏鬥時,阿修打電話到店裏,哭說他在家樓下看到什麼先生倒下了,嚇得我立即趕回家樓下。只見他穿着黃色雨褸狼狽地在馬路中央,拚命抓着被風吹倒的白色頭黃色身安全島,信我,既然那是場連安全島都可以擊倒的暴風,那麼要捲走一個五歲小孩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我跑過去一手抱起阿修,連開口責罵都來不及,這傢伙已先聲奪人「哇」一聲哭了出來,哽咽着:「安全島先生倒了,我一個人救不了『他』……」這孩子大概是聽我說太多死物會說話的故事,才認定安全島是一位「先生」,而「他」快要被「杜鵑」殺死了。
「那種東西要死不讓『他』去死啊?」我當時這麼吼了一句,就抓起這小子上樓。
往後的幾小時,他都不跟我說話,洗澡、吃飯、寫作業都眼眶含着一泡淚珠。還記得我拒絕讓他收養那隻常來舖頭搗亂的野貓,突然失蹤了之後,這孩子已很久沒對我哭着要求什麼。最後我還是屈服,冒着雨把那個比五歲阿修還要重的政府公物「擄了」(阿修說是「救了」)回家。
阿修每天放學就會問我,安全島先生今天有沒有跟我說過話(因為阿修沒有聽到物件說話的能力)。但我極其量只聽到「他」發出「唓嘞」的聲音,「唓嘞」、「唓嘞」一整個下午。阿修總是不厭其煩,對着裝上了燈泡的安全島先生自言自語,安全島卻只是沉默被阿修「唓嘞」、「唓嘞」玩弄着開關,沒什麼回應。有一天我隱約聽到阿修問安全島有沒有見過小黑……大概就是那隻我不讓他收養的四蹄踏雪流浪貓吧?原來他給貓咪起了這普通到爆的名字。我狠下心,跟阿修說,也許安全島先生本來就不會說話,所以別煩「他」了。接着我們吵了幾句,阿修哭喪着臉地說我是大話精,猛力把安全島先生推倒,「砰磅」一聲摔在我腳上,然後奪門而出。
「唓嘞……」安全島又發出了聲響。「黑色身白色腳的貓咪啊,是指扁扁嗎?」媽啊,這傢伙非要等到我們表兄弟決裂才哼半句啊?
「『唓嘞』……那隻黑身白腳貓,和很多貓一樣,總愛在我身上撒尿,『唓嘞』……」我抓着腳叫痛,啐,「唓嘞」什麼啊?還裝什麼cute,給貓咪改個名字作「扁扁」?
「因為牠們有些被車子撞飛,有些被捲進車底拖行不知到哪裏,有些像扁扁一樣,被一架車撞過之後,再被很多車輾過,『唓嘞』、『唓嘞』……壓得扁扁的,毛茸茸的、混着血、扁扁的一塊……」
原來安全島在我們樓下站了十幾年,安全島並不像其他物件般有「主人」,「他」只是件公物。每天人來人往經過,短暫停留在「他」身邊,卻從來沒人對「他」認真看一眼。偶爾親近「他」,停留在「他」身邊的,就只有流浪貓和狗,但隨着這條街的車子愈來愈多,幾乎每隔兩三個星期,就會目睹親近「他」的貓咪或小狗變成「扁扁」。每次聽到骨肉被輾過的「唓嘞」「唓嘞」聲,「他」都期望讓自己快點折舊被換掉。好不容易遇上颱風,「他」心想,這下真的可以完了,卻被我們拾了回來。重新接上電之後,「他」記得最清楚的聲音,就只有「唓嘞」。直到阿修反反覆覆跟「他」提起貓咪,「他」才猜想,阿修說的小黑會不會就是其中一隻扁扁貓。
我覺得這一切,只是一堆巧合。
我把安全島先生扶正,「他」問:「你要告訴那孩子嗎?」我當時覺得安全島先生太小看阿修了,阿修是任性又愛哭愛鬧,但我以為,他比一般的五歲小孩更了解死亡的意思。我甚至認為這個在燒炭自殺的父母懷中掙脫出來也沒哭過的命硬小孩,大概不會為壓扁了的貓咪太過傷心。待阿修餓了回家之後,我就輕率地把安全島先生的話一五一十說給他聽。我還哄說,那也沒法肯定那就是小黑,他卻自言自語地說那麼多扁扁貓好可憐,看着扁扁貓死去的安全島先生也好可憐……然後就一發不可收拾地哭了起來。喂喂喂,哭什麼?難道我這樣無父無母的好青年,要照顧你這無父無母的臭屁小孩就不可憐了麼?
我真後悔我因為這一瞬間的想法,任他哭下去。
結果,整整一個月,阿修不停地哭,彷彿要把人生流淚的配額統統一次過用盡似的。之後我用盡方法哄他罵他都不收聲,直到一天我都受不住崩潰,像婆媽連續劇哭着求他不要哭。終於,他呆呆地看着我,跟我說「對不起」。我實在搞不懂這五歲小孩傷心的準則,但我記得,這是他清楚地說出口的最後一句話。
隔天,他就像平常一樣,很乖的上學,自己洗澡、吃飯、寫作業,異常地安靜和乖巧。我因為忙着店裏的事一直都沒留意,過了好一陣子,直到老師跟我說他在校幾乎都不說話,我才驚覺要帶他去看醫生,結果發現他聲帶上,長了個已不能切除的繭。
「你在發什麼呆?有什麼『東西』跟你說話了?」 阿修用手語跟我比着。這時,阿修屁股下的安全島先生,發出了「唓嘞」的聲響。
「安全島先生說快受不住,你的笨屁股快把『他』壓死了……」我苦笑道。
看着現在坐在安全島上踢着腿的阿修,我在想,若我沒告訴阿修任何關於物件會說話的事,也許他就不會被奇怪的想法困擾,也可能不會失了控的哭破嗓子,像普通小孩一樣健健康康的成長了……
阿修看着我,彷彿讀到我心裏在想什麼。
「沒這種事啦……」他比了比手語,猛地從安全島先生跳下,積水濺了我一身一臉。
這混蛋,一定是故意的。

 Bookmark
Book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