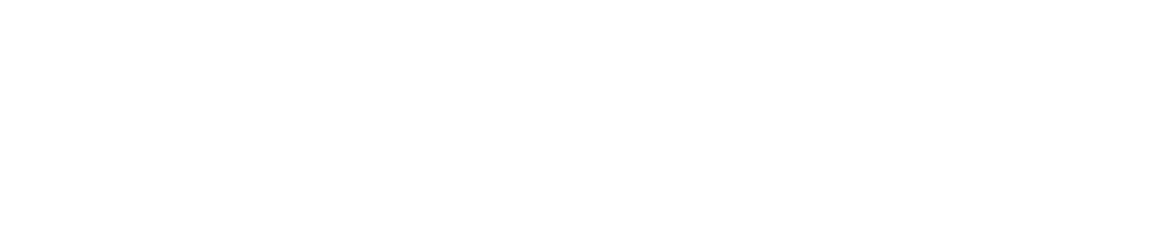在我把衣服晾在窗戶外面的時候,突然想起,十二歲那年的某個下午,我發現有一個不屬於我母親的粉色蕾絲胸罩,懸掛在我家晾衣的竹杆上;呃,該說是被撕扯得不成型狀的,「垂死的躺」在曬得發滾的竹子上。我本打算使用晾衣服的叉子把它撥開,讓它飄到別的樓層,或是乾脆墜落 到大街上,免得它的主人來按我家門鈴。那時才十二歲的我,對會穿那種香艷胸罩的女人,並沒有太多幻想。當我揮動叉子的時候,那個傢伙淒厲地叫了一聲,我裝作聽不見猛地想將它弄走,直到它終於說出:「嘿,你不是聽到我說話嗎?我有話跟你說……」
「又來了。」我心中納悶。那不是我第一次聽到有「東西」跟我在說話。那些俳迴生死邊緣的「東西」,遇上我這個偶爾聽得見它們的倒霉人類,總會興奮地喋喋不休說個不停,不理人感受……但它們不過是物件,人類尚且不會在意別人的感受,若要求被人類折騰至垂死的物件,能體貼地照顧我這陌生人的感受,也太牽強、太不顧及這些可憐傢伙的感受了。但我記得這破爛胸罩的原因,是它話不多。
胸罩說它是樓上某戶的女主人的私人物品。「我看得出啊。」我繼續裝作很忙地晾衣服,不想搭訕下去,在這之前我有太多次,顧著跟物件閒聊,令周遭的人以為我是傻瓜的經驗。
它說它的主人很愛它,會穿著它照鏡子,照上好幾個小時,也捨不得脫下。「哦,是嗎?那你為什麼在這裡?」我敷衍著它。
它沉默了好一陣子。「你被拋棄了吧?」它的沉默令我很好奇,尤其它激動地否認,然後又再度沉默。根據我的目測,它的主人該是個胸脯很小的女人,我不禁安慰它說,胸脯很小的女人一旦覺得舊胸罩變沒有彈性,不能把僅餘的脂肪擠在一起,就會覺得它不中用了,丟掉也很正常,並不是每個女人都像我媽般節儉……它激動打斷我的話,說它是主人最珍視的一個胸罩,是主人約見男人的戰衣,它主人很喜歡把內衣當成外衣的一部分,外露出來。雖然它直至現在垂死,也從來沒有被男人溫柔地解開過,也許是因為它的主人,早已到達被現在的人稱呼為「中女」的年紀。(當我十二歲的時候,「中女」這稱謂還沒有流行起來。)我真的不太好奇「中女」獨守閨房的話題,我在想是不是該找個時機可以一叉子把它打發走,只是我的手不夠長也不夠力氣,把竹子遞到它的所在位置。
它並沒有發現我的意圖,繼續說著,在被撕破的前一刻,它感受到主人的心跳激烈加速,於是它更緊緊地保護著主人的胸脯。之後它的主人被男人逼至天台的邊緣,它便被一雙瘦弱但有力的手,粗暴撕扯掉,從天台飛墮到我家窗前,它的主人被按在在天台的水箱……
「哦,是嗎?」我把衣架綁上竹杆,使勁一揮,胸罩嗚嘩一聲,飄到別的地方去了。接下去,它本來是想說什麼的呢?
過不了兩三天,我媽發現我家的自來水,有一股腐臭,我就知道那爛鬼胸罩本來是想說什麼了。我告訴我媽,因為有個女人被藏在我們這棟唐樓的水箱裡。我媽最初並不相信,但還是找人去看了…… 總之,之後這件事被上了報紙,說那個女人被暗戀她的同事姦殺,然後被藏在水箱裡,泡了好幾天。我媽知道真相後,嘔吐了好幾天,也改掉了從前有生喝自來水的習慣。
類似的事,後來不停發生,我被街坊稱為「常常發現屍體的自閉男孩」。真是個不光彩的稱呼。
他們說這是一種才能。老實說,我並不是很熱衷當發現屍體是一種才能。
那個時候的我,寧願擁有什麼別的能力……例如能背好所有超過三個英文字母以上的生字,又或者學會把電郵的「郵」字不再寫成「陲」字。
我希望我能寫不太難看的字,那至少我能把我自己寫的帳簿看懂,能較有系統地整理一下店裡的帳目。如果我能閱讀或書寫超過三行以上的文字,那我大概可以像很多人一樣,完成初中,甚至高中。也可以不繼承我父這間二手雜貨店,找一份比較像樣的工作。我有嚴重的讀寫障礙,你現在看的文字,並不是我寫的,是比我小十二年的小表弟,聽我的口述而寫的。你也許不相信,我的另一項技能是,我很容易能學會說和聽不同語言,但就是怎樣都學不會寫;而我的表弟是個寫字很漂亮的男孩,但就是不會說。因為他的聲帶長了一個沒法切除的繭,令他連發出聲音都不能。我爸說上天喜歡愚弄我們這些在地上卑微行走的人類,給每個人分配某些技能,並附送一籮筐的缺陷。
我被分配了一項無聊的技能,那就是我聽得到垂死的物件說話。
有些人或者會問,物件會說話嗎?但當我幼稚園高班時第一次聽到,那破洞破得幾乎四隻腳趾都穿得過的白襪(左腳)突然尖叫:「我快要死了……」我第一個反應卻是:「物件會死嗎?」
嗯,物件是會死的,而且它們知道自己快要死。因為接著我便因太害怕,把白襪(左腳)剪碎,殺死了。當時,完好無缺的白襪(右腳)對於缺了拍檔並沒有意見,大概它也明白,白襪只要是白色的,都能和其他的白襪配成一對嘛。
我們不能否認,任何人都曾經有意無意摧毀(殺死)一些物件。只是沒什麼人會認同,一直被認為沒有生命的「東西」,其實也是會死亡的。
Storyteller:Heiward Mak 麥曦茵
Illustration : Light Man

 Bookmark
Bookmark